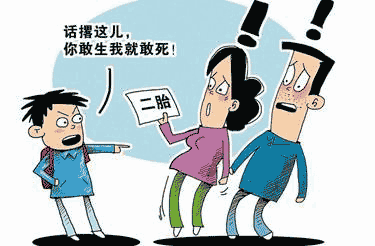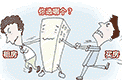今年是基本法颁布25周年,也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30周年。基本法的起草过程是香港回归祖国的一段重要历史,作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之一,笔者在此记下当年工作的一些回忆与感受,以志纪念。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1985年4月16日,第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批准中英联合声明及其附件的同时,决定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同年6月18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共59人,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担任主任委员。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来自内地与香港,在组合上各有不同特点。内地委员中有不少知名专家学者,如费孝通先生是我国社会学大师,钱伟长先生是著名科学家。至于许崇德、萧蔚云、吴建璠、邵天任则是内地著名法学专家,后来更被称为基本法“四大护法”,广为港人熟悉。值得一提的是,许崇德与项淳一、王汉斌、胡绳、张友渔这些内地委员都曾经参与1982年中国宪法的大规模修改工作,是名副其实的宪法专家。
香港的23名委员来自不同社会界别阶层,可谓香港社会的一个缩影。笔者当年35岁,是所有草委中最年轻的,也是唯一来自劳工界的香港委员。能够参与基本法起草工作,为香港回归略尽绵力,笔者深以为幸。在起草工作中,通过不断学习,以及和内地法律专家交流讨论,笔者对宪制性法律及其草拟方面的认识也从零开始,有了极大的提高。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工作过程中十分重视香港社会的意见。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就决定委托在香港的委员发起筹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谘委人数约200人,比草委多出不少,社会代表性更广,可以让港人意见更有效地反映到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中。另外,起草委员会也十分重视信息公开透明,每次会议之后都举行记者发布,由内地与香港两地的代表共同向传媒介绍会议情况、讨论的内容等,这在当时内地的立法工作中是罕见的。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基本法不仅是香港的基本大法,也是一部全国适用的法律,因此委员会选择在内地不同城市举行会议,如昆明、厦门、广州、珠海等,目的是向内地人民宣传基本法的重要性。
起草委员会在通过基本法的草案稿时,条文是逐项表决的,包括相关修订,而表决是以不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获全体委员三分之二多数支持才通过。只要多于三分之一委员反对,任何条文都不可能通过。由此我们就能明白,在政制问题上,若非有内地委员支持,有关两个普选的条文根本不可能写入基本法内。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英联合声明只规定了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而立法机关也只是由选举产生,并没有达至两个普选的规定,因此,基本法写下了最终达至两个普选的目标,是比中英联合声明走前了一大步。
事实上,和联合声明比较,当时基本法的起草可以用“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来形容,因为一切关乎港人对前途的信心,起草委员会的处理十分慎重。例如,有关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的居留权,以及港人在香港以外所生子女的居留权两个问题,其实当时委员会完全了解,照搬联合声明写法有可能引起解释的问题,但如果改变写法,恐怕只会造成不必要揣测,后果更不理想,因此委员会采取了原文照录的做法。另外,基本法第三章的标题是“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显然,权利与义务是相对的,有权利就有义务,两者不能偏废,但这一章总共有十九条,当中用了十八条订立林林种种的权利,只有最后一条是关于义务的,但也只不过是规定居民有遵守法律的义务而已。
基本法起草工作面对不同方面的关注和诉求,涉及问题十分重要,但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体现了力争共识、愿意妥协的精神。如第23条规定由特区自行立法保障国家安全。第158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有最终解释权,同时赋权特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可以解释基本法。除此以外,基本法还规定,人大常委会发回特区的立法,对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作出增减,或对基本法作出解释之前,须征询基本法委员会意见,而基本法的修改议案列入全国人大的议程前,也须由基本法委员会研究并提出意见。这些安排同样是为照顾不同方面关注——包括一些港人的忧虑——而得出的妥协方案。
笔者认为,基本法的起草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准确理解基本法的钥匙,也为我们提供了解决政治分歧的经验和智慧。邓小平先生在1990年会见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说过,基本法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的确,基本法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智慧结晶,我们就是依靠这种智慧克服困难和分歧,找到共识,开创了“一国两制”的伟大工程。对今天处于政制发展关键阶段的香港社会来讲,这种智慧可谓历久常新、足堪借鉴。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